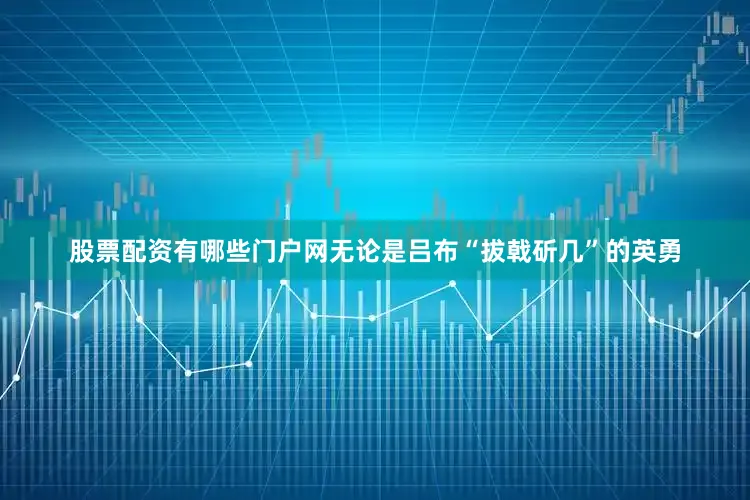
如果用网络小说中神格的视角来观察这些古代武器及其所承载的文化意义,确实别有一番趣味。戈,是战争的象征,至少可以视为一级神;斧钺则代表着权威和惩戒,有时甚至堪称神王级别的存在;战锤更是分量十足,作为身份和权力的象征,某种意义上它就是神格本身,无论古希腊哪个神掌管什么,战锤代表的就是“已经成神”的地位。即使是像鞭锏这类武器,搭配两位门神的合体形象,也能驱除邪祟,保护千千万万的百姓。相比之下,戟的地位就显得低了许多,作为高官门前的侍卫武器,纯粹是个“打工仔”,这种神格差距几乎可以说是“一点点”变成了天壤之别。
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戈的继承者之一、五兵之一的戟,本不应落得如此惨淡的境地。论武器性能,戟能长能短,功能多样,是少见的多面手;论历史,从春秋战国到两晋,近千年的时间里,戟都有着不俗的地位。无论是吕布“拔戟斫几”的英勇,还是孙权“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的防备,都彰显了戟的历史厚重。长戟或短戟,其源远流长的历史令人敬畏。然而最终戟不仅没能成为战争主力,甚至连武器或战斗力的地位都没占据,最终沦为侍卫级别,这其中的原因,还得从使用技巧和武器演变的细节说起。
展开剩余77%长矛作为一种费力的杠杆武器,操控起来并不简单。在青铜时代,青铜矛头笨重,长矛的攻防动作显得非常迟缓不灵活。但进入铁器时代后,矛头重量大幅减轻,长矛的攻防能力立刻变得敏捷而致命。长矛对阵长矛时,如何抓住对方的矛头、把身体隐藏在矛杆后方,成为重要的技巧。王堡枪的起手势中就有这种藏身于杆后的含义。《箭士柳白猿》中,于成惠和徒弟们对抡长枪,实际上是在互相试图捕捉对方的枪头,让自己的枪杆形成省力杠杆。电影对此有些夸张,但其中的技击思路确实存在。知道怎么打是一回事,做到却是另一回事,没个几十年功力,普通士兵很难达到于老那种枪术水平。
既然做到难度大,便有人想出捷径——给长矛加装小枝,用小枝主动去钩住对方矛头。戟从青铜时代能刺能砍,变成汉代那种带有小枝的形态,就是因为这个需求。汉代沿袭了青铜戟能刺能砍的传统武器,现代学者称之为钺戟。这种戟在博物馆或藏家手中稀少,说明在当时并不流行,至少不如主流的卜字戟受欢迎。可见,到了汉代,“能刺能砍”已经不算最核心的属性,而用小枝抓住对手攻击明显更受欢迎。
从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出土的战国铁戟开始,戟的小枝最初没有特定朝向,到了汉代骑兵用的戟,小枝又有了朝向,不过朝向是向上的,这种戟称为马戟。与标准卜字戟相比,马戟的横枝向外弧度明显,显示其“啄杀”功能在东汉时期已明显弱化,而用小枝去接触和“拒止”对手的用途则更为普遍。
魏晋时期,单靠弧度的横枝已不足以有效抓住对手的矛头,横枝演变成向上的“叉”,这让戟在长枪防御动作中更易“拦”、“拿”住敌方长矛,戟的防御作用有所加强。但无论是小枝、叉子还是丩字戟,要提高成功拦截对手的几率,仍然需要高超技巧作为支撑。
许多热爱“兵击”的朋友表示这些动作根本难以发挥,甚至觉得累赘,这一点无可厚非。毕竟现代兵击爱好者无论怎么练,也难以达到古代士兵拼命厮杀时的水平。不过他们的体验也证明了,用小枝拦截长矛确实有技术门槛,属于“有用但不完全好用”。因此到了宋代,镋钯的出现成了戟的替代品。
镋钯操作更加便捷,戚继光改良鸳鸯阵时,将两把长矛换成镋钯,专门用于防御。有了这个替代品,传统戟逐渐失去了存在价值。《宋史·仪卫制》中记载,戟变成了“戟,有枝兵也。木为刃,赤质,画云气”,彻底转为礼仪兵器。可以说,戟作为实战武器在宋代已经走到了尽头,变成工艺品。可是戟在汉代形成的文化象征已经深入人心,名字不轻易消亡,“能刺能砍,防御方便”的长柄武器仍需存在,演变出带斧头的刺击武器,顶着“戟”的名号活到了现代,那就是戟刀。
做品牌的人都明白,一个品牌想成为经典,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历久弥新。像“全聚德”“同仁堂”这类百年老字号,无需多言,跨越代际传承令人印象深刻。关键在于不改名字,让顾客的祖辈都认识、信赖,这才算成功。
而戟,却成了品牌反面教材:联装戟、卜子戟、仪仗戟,甚至借用“戟刀”名义的武器,除了这些主流形态外,能刺能砍的青铜戟还有很多“孩子”,但大多数没有机会多次迭代,逐渐被淘汰。比如鸡鸣戟和它的欧洲同类,这对“难兄难弟”用途太过特殊,最终边缘化。唯一稍作演变的马戟,到唐中期也被淘汰,只留下名字,后代武器则趋向趋同进化。
某种武器形成文化意象相对容易,关键是用得久,还要被人牢记。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戟经历了无数身份的转变和文化内涵的重塑。尽管名字未变,形制却千变万化,以至于古人都难以确切定义“戟”究竟应为何种形制。每当提起戟,人们脑海中浮现的往往不是战场上纵横驰骋的戟,也非贵族手中把玩的戟,而是那排成整齐队伍、作为威严象征摆放在门前的戟。久而久之,门前列戟深入人心,使戟成为了侍卫身份的象征。
发布于:天津市正规配资平台官方,配资之家80809配资,股票十倍杠杆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